尼伦
蒙古
基因家族介绍
家族遗传标记为 C-Y4569,共祖时间约为 1190 年前,推测为尼伦蒙古。
溯源分析

形成时间
根据推算,C-Y4569 类型共祖于大约 1190 年前,即共同祖先生活在唐末五代时期。

支系情况
Y 单倍群 C2a-F3796(星簇)(原名 C3*-星簇,下文简称“星簇”)是蒙古语人群的核心父系类型之一,广泛分布于所有蒙古语族群中。该类型由 Zerjal 等学者于 2002 年首次识别,研究者发现其 Y-STR 网络呈星状扩张形态,共祖年代较晚(1000±300 年前),据此认为,这一遗传扩张与 13 世纪蒙古帝国崛起直接相关,可能源于成吉思汗或其男性亲属的父系。
后续研究表明,星簇在黑龙江至里海的广大区域内频率显著(约 8%),其分布范围与蒙古帝国疆域高度重合,最晚共祖时间(约公元 700-1300 年)亦与成吉思汗时代(1162-1227)接近。阿富汗哈扎拉人(传为蒙古驻军后裔)中的高频现象亦支持其与蒙古扩张的关联。韦兰海等学者通过对欧亚东部 238 个人群的 2266 例 C-M130 样本分析,确认 701 例属此类型,其中 420 例完整数据单倍型在 Y-STR 网络图中形成独立簇群,显示出剧烈扩张特征。该类型在哈萨克人中频率最高(在 7 个人群中占比超 50%,13 个人群中超 25%),集中于大帐部落及克烈部;蒙古、布里亚特-巴尔虎、乌兹别克等族群次之,非阿尔泰语系人群中则极少见。
根据23魔方现有样本及树形分析,尼伦蒙古主体应对应 C2a-F3796 下游 C-Y4569(即本研究所涉家族)。
根据目前相关科研机构所提供的信息,对拙赤合撒儿(成吉思汗同母弟)、合赤温(成吉思汗同母弟)及别勒古台(成吉思汗异母弟)后裔的相关研究线索亦指向 C-Y4541,尚有待样本进一步增加以资明确。
综合公开发表的其他有关星簇的文献,我们发现目前可见的星簇高频的人群均可追溯到尼伦蒙古部:
1)乌兹别克人的曼格特部、格尼格斯部。曼格特部(Manghit)源自尼伦蒙古部的分支部落忙忽惕,他们随术赤的军队西迁并生活在金帐汗国内部。据《金帐汗国兴衰史》,金帐汗国在 1219-1502 年之间统治了欧洲东北部和中亚地区,此时期曼格特部的首领极大程度地参与了金帐汗国的政治事务。最初,曼格特部支持也迪该建立了在金帐汗国内部半独立的诺盖斡耳朵(Nogai Horde)。在谢赫马麦(1541-1549)时期,东部诺盖脱离了原来的诺盖斡耳朵,即阿尔特吾勒诺盖(六子诺盖),并在北咸海周边建立了自己的斡耳朵(即阿尔特吾勒斡耳朵),后部分部众于 16 世纪因战乱向南迁徙至河中地区,成为游牧乌兹别克人(后世成为乌孜别克人的主源)的一部分,其他没有参与迁徙的曼格特部最终成为卡拉卡尔帕克人五部落中的一个大部落。通过细化研究,曼格特部属于本研究所涉家族下游 C-BY182928。根据史料记载,格尼格斯(格泥格思)部也是尼伦蒙古的分支。在 13 世纪早期,格尼格斯部作为术赤的四个属部之一被派往金帐汗国。金帐汗国崩溃之后,格尼格斯部的一部分也向南迁到河中地区,留居花剌子模的主体最后成为卡拉卡尔帕克人的一部。Sabitov 等人报道的格尼格斯部样本中的 3 个属于星簇。格尼格斯部中的其他样本,根据 Y-STR 可以推测属于高加索地区常见的 G2a-P15。可见,星簇是格尼格斯部中唯一可以追溯到东方的父系类型。
2)哈萨克大帐诸部。在东察合台汗国(或称蒙兀儿汗国)后期,很多蒙古起源的部落都加入了新兴的哈萨克汗国,包括许兀慎部、札剌亦儿部和朵豁刺惕部等。随后,他们成为现代哈萨克“大帐”(Great Jüz,又译大玉兹)中的玉孙(Uisun,与汉代乌孙无关)、札剌亦儿(Jalayir)和杜拉特(Dulat)等部落。不过,对于哈萨克现今的部落是否是上述蒙古部落的直接后裔还有部分争议。根据 Zhabagin 等学者 2020 年的研究,C2-F3756 在以上诸部中均有极高占比(玉孙 313 例中占比 46.6%,札剌亦儿 117 例中占 37.6%,杜拉特 159 例中占 48.4%)。最近细化研究显示,哈萨克玉孙部主体属于本研究所涉家族下游 C-Y12782。(在哈萨克人的克烈[Kerey]部中也观察到了非常高频的星簇。哈萨克人的谱系记录之中有关克烈诸部的起源有多种且互相矛盾,据哈萨克斯坦相关细化研究,克烈-阿什迈勒[Ashamaily]部属于本研究所涉家族下游 C-FT224144,确系玉孙部分化而来;克烈-阿巴克[Abaq]则属于另一下游 C-FT411734。)
3)哈扎拉人。在 Zerjal 等人早年的研究中,哈扎拉人被认为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因此成为支持其结论的重要证据之一。但是 Zejal 等人引用的文献本身即说明哈扎拉人是成吉思汗派往阿富汗地区的驻军集团的后裔,而不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男性的后裔。据《史集》记载,蒙哥合罕把“忻都斯坦与呼罗珊交界之处”的 2 万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撒里那颜,并要求他永远驻扎在那里。在印度莫卧儿帝国创立者巴布尔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阿富汗东南部地区的哈扎拉人。这些被派往阿富汗的驻军主要是普通的蒙古士兵,也可能包括被征服的其他部落的士兵。通过细化研究,星簇下的哈扎拉人主要集中于本研究所涉家族下游 C-SK1076 支系。
据《史集》记载,尼伦蒙古与迭儿列勤蒙古构成了原蒙古主体。蒙古帝国时期,尼伦部族构成军事主力,并被分遣各地戍守,形成了前述诸族群的基础。当前证据支持星簇的扩散源于尼伦蒙古部的历史活动,但成吉思汗本人的直接关联仍需通过更多可信谱系的后裔样本验证。
C-Y4569 类型的具体源流有待进一步探索,留待后续研究。本研究因检测样本有限,尚需更多用户参与深度检测,以使该家族的谱系树和共祖时间更精细准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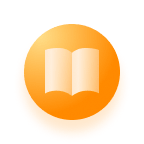
家族情况介绍
尼伦(Nirun,又译尼鲁温,意为“腰脊/山腰”)蒙古与迭儿列勤(Darligin,又译迭列斤,意为“沿山岭”)蒙古构成了现代蒙古语人群的主要族源基础。根据《蒙古秘史》记载,尼伦蒙古诸部的始祖母阿阑豁阿,为豁里秃马敦部首领豁里剌儿台篾儿干之女,出生于豁罗剌思部,嫁给朵奔篾儿干,生有二子,长子博寒葛答黑(又作别勒古勒台),次子博合睹撒里直(又作不古讷台)。朵奔篾儿干死后,阿阑豁阿寡居,每夜有个明亮的黄色的人,循着天窗或门额射入的光芒而进来。抚摸着她的肚子,使其光芒透进她的肚里。出去时,在日月的光照下,如同黄狗一般,摇摆着悄悄地跃走。由此生下三子,分别是不忽合答吉、不合秃撒勒只和孛端察儿(成吉思汗十世祖),该传说成为蒙古族源神话中“感生说”的核心内容。这一叙事通过"腰脊诞生"的隐喻,强调其血统的神圣性与纯洁性,为成吉思汗家族统治合法性提供依据。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进一步将尼伦蒙古的起源追溯至额儿古涅昆西迁事件,并提出了“尼伦-迭儿列勤”的二分框架。据《蒙古秘史》与《史集》记载,尼伦蒙古始祖孛端察儿三兄弟约生活于 10 世纪初,至成吉思汗出生(1162 年)时,已发展为包含 24 个分支的庞大部落集团。
在成吉思汗先代世系与诸部关系的问题上,《史集》与《元朝秘史》等史料的记载存在诸多矛盾。《元朝秘史》强调以成吉思汗直系先祖为核心的紧密血缘网络,而《史集》则提出“尼伦-迭儿列勤”二分法,从而将各部族划分为不同集团(如别速惕、巴鲁剌思属尼伦;斡罗那儿、晃豁坛属迭列列斤;雪尼惕属突厥部落)。两部史书在朵儿边、兀良合、雪尼惕等部族的归属上分歧明显。此外,《史集》自身还记载了一种“异说”,列举了包括晃豁坛、雪你惕、八鲁剌思等十二部为同源亲属,此说与《秘史》的部族同源记载高度吻合,却与《史集》主流的二分法冲突。这些矛盾反映了“圈层结构”的建构本质:蒙元时代史家以成吉思汗家族神圣世系为核心,依据血缘亲疏将各部族编织成中心(黄金家族)-边缘的层级结构。此结构依赖于对绵长父系世系的塑造(如突出孛端察儿的神圣性,缩小阿阑豁阿感光生子的范围)和对兄弟祖源传说(如朵儿边“四兄弟”、克烈“七子”、弘吉剌“金器三子”)的边缘化处理。这些世系的形成过程存在政治性的重塑,从而服务于黄金家族的神权统治需要。《史集》的尼伦-迭列斤分类可能源于地形概念(走出额儿古涅昆的传说),最初无关血缘,后在成吉思汗崛起过程中被赋予建构血缘谱系的功能,用以整合新附部族并淡化传统强部(如札答阑、泰赤乌)的独立性。现有证据表明,《史集》编纂者拉施特并非依据单一史料,而是整合了多种来源:既有类似“金册”(篇幅有限,侧重世系录和异密名录)的系谱材料,也有《脱必赤颜》等叙事性史料,并通过考辨与嫁接(如用额儿古涅昆传说中的“尼伦”替换感生传说中的“腹”),将原本独立的传说(走出群山与感光生子)熔铸成连贯的起源叙事,最终服务于伊利汗国时期对蒙古正统历史的重构。(编引自张晓慧《追本塑源:元朝的开国故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社区讨论
查看更多
参与讨论 ......